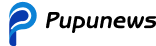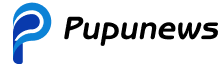誰沒流浪過?
有人從李白六十一歲的詩文中做了統計,他一生中就花了二十七年流浪四方,攀登過八十多座山,跨越了十八個省,總共到過二百零六個州縣,遊覽了六十多條江河溪,和二十多個湖潭,幾乎等同於流浪了半個中國。
雖然有說法,李白的出生是綿州昌隆縣青蓮場,也就是今天屬於四川的江油,不過另一說法是生於中亞碎葉城,也就是今天屬於吉爾吉斯斯坦的地方,可是由他的詩文中卻對應不到他的出生地,也就是說,李白似乎在一生中都在尋找他的故鄉,也就是將異鄉當故鄉一樣地流浪著尋找。
他一直都是用行走流浪嗎?
又背負著多少行囊呢?
誰又沒流浪過?
流浪的人都會帶著家當,所有的家當。
大的小的,輕的重的,方的圓的,乾的濕的,緊的鬆的,貴的賤的,吃的穿的,喝的睡的等等,只要凡是還能讓自己活下來的,都是。
在一個城市公園裡,見到一個流浪漢,他們說是街友,但這裡沒有街道,只有到公園散心,和運動的城市人,還有流浪為家的流浪漢。
公園,應該是他的家吧,一個流浪漢的家。
一眼看見他時,先觸目驚心於他的家當,所有大的小的,輕的重的,方的圓的,乾的溼的,緊的鬆的,貴的賤的,吃的穿的,喝的睡的等等,家當都在一輛單車周圍,以及車後跟隨著一個行李箱,和拼接起來的菜籃拉車上,因為多了幾個小輪子,因此不致讓所有的家當壓垮自己的身子。
一隻流浪狗看也不看一眼,慢悠悠走過那一長列家當,走遠了。
如此長長的一列家當,幾乎管了流浪時所有基本的生活了。
城市人似乎並不在意這流浪漢所有的家當,以及是哪些家當,或多少家當,如果在城市住久了,也會有意無意地將眼光視線避開。
不過,流浪漢並無法避開生活,眼光,以及城市公園,還有那所有的家當。
所以,為了生活所需,或別的,流浪漢大多只能選擇城市公園為家,或歇息,繫帶一長列不能丟棄的家當,讓自己有較多的時間自適自在。
他流浪過多少地方了呢?
又流浪過多少歲月了呢?
我見到的流浪漢背著我而坐,背後是那一長列不能丟棄的家當,但誰對這些家當也看不上眼吧。
他穿著老舊的深灰色外套,戴著比外套稍淺一些灰色的毛線帽,壓低著頭,因此我又見到他圍著一條紅白相間的蘇格蘭格子圍巾,這是一個冬日,城市公園的人稀微,流浪狗也是。
我見不到他的臉,而他面對的是遠遠的幾株榕樹,一片矮樹叢,與稍遠的高高橫橫河邊雜亂芒草,和已顯出柔亮的冬日,以及冷冷靜寂寂的風。
他一直坐在那裡,享受與他人一樣的冬日,那會讓他稍稍溫暖一些吧。
不知他曾經如何流浪的,未來還如何流浪,如今暫時坐在冬陽中,起身後還如何流浪,而誰也不會在意他的流浪歲月吧。
然而,誰沒流浪過呢?
有的人是身在流浪,但心很安定,而有的人相反,或是有的人身心都不安定地在流浪。
這城市公園是他,與其他流浪漢暫時的家,也是拖著一列長長家當暫時的家,在這家裡可以暫時避開許多城市額外多餘的眼光,與憐憫,或感觸,還有更多的想法,現在,他只想安靜地一個人曬曬冬陽,讓一列長長的家當也曬曬而已吧。
風,在晨光逐漸升起之後,於四周的野草上輕柔地彈唱,也在那一列長長家當的塑料袋上輕輕晃動著試圖打開它,我能感覺家當的塑料袋裡灌滿了風,但顯然彼時還不是帶著風去流浪的時候,他需要歇息。
那一隻原本已走遠的流浪狗,不知何故,又轉回來了,轉頭看看看似出神的他,與身後那長長一列家當一眼,還是走遠了。
這是一個我曾經很熟悉的城市公園,包括流浪風,流浪狗,也很眼熟地經常見到流浪漢,和不同的卻很相近的長長一列列家當。
只是,我也在一旁,遠遠地看著他,或其他流浪漢,還有那不同的卻很相近的長長一列列家當,出神。
我忽然感覺,自己似乎也不斷在歲月旅途中到處流浪,只為被迫似的追索某些生活需要,而拖著與流浪漢不同的卻很相近的長長一列列家當,與疲累,在不同的地方走走停停,而安定不得,而渴望有一方夢土。
但或許,我們凡人也都在紅塵裡流浪中,如享用追索某些需要的一種孤獨感,那如一種迷藥,會上癮,有時卻又致人清醒,且猶豫,傷痛著,有時更覺得帶著自己的家當,努力試著找到自己流浪的位置,覺得那也是一種生命動力的享受。
不知李白是怎麼想的。
流浪中享有的孤獨,讓享受的人會有如吃了迷藥而上癮,李白也會嗎?
我曾在不同的時空歲月中流浪,感受孤獨,感受疲累,和無緣由的出神,也享受那一種如同吃了迷藥般的別樣繾綣縈繞,其中更有某樣飄零,又夾雜著果敢的況味,令人暗暗著迷。
只不過,到最後有人選擇繼續,有人選擇停止罷了。
有人一生皆未踏出過大山,心中卻可能流浪在另一座大山。
於是,流浪之必要,或人人有之。
暮色近了,寂然近了。
那流浪漢並沒有離去的意思。
但周遭有點寒意了。
我起身,緩步往回走,風在我身後流浪,雲也是,冬陽也是,芒花也是,河流也是,那紅白相間的蘇格蘭格子圍巾也是。
抬起眼,稀疏的點點燈光已在公園外遠遠的塵間中亮起。
Advertisement
Advertisement
Advertisement
Advertisement